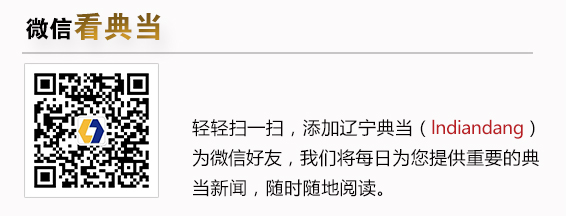刘忆如:存保制度是民营银行推出的前提
发布时间2014年01月10日浏览量:来源:辽宁典当网作者:杨燕青 严婷 第一财经日报
分享到:
“金融特别敏感,牵一发动全身。所以中国金融市场化开放,最需要注意的是顺序和速度。”台湾前财政部门负责人、现任香港北威国际集团董事总经理刘忆如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台湾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为中国大陆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谈到汇率和利率改革,刘忆如强调,不能因为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影响到整体经济政策。而低利率环境对利率改革比较有利。
她认为,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1万亿元是个很重要的门槛,意味着已经达到规模经济的程度,开始出现这个货币的衍生性商品,出现市场化的离岸利率,从而构成套利空间,迫使货币加快市场化进程。而大陆目前刚刚过了这个门槛。
关于银行准入,刘忆如认为,不宜太快放开,要有一定顺序。而一个好的存款保险制度安排很重要,更是民营银行准入的前提。
汇率改革需考虑整体利益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大陆正在推进包括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一系列金融改革。中国台湾在各项改革上都有不少相关的经验和教训。你认为台湾的经验对于大陆未来几年的改革有何借鉴意义?
刘忆如:我认为在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开放过程中,金融通常都放在最后一块,因为金融特别敏感,牵一发动全身。所以中国金融市场化开放,最需要注意的是顺序和速度。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像拉丁美洲在上世纪80年代金融开放时速度没有放对、顺序有点混乱。目前看来,大陆的基本方向是对的,顺序上也很注意。可因为外界的期待很高,不能等大陆慢慢地一步步来。例如利率市场化通常是优先于资本市场化改革,或者说是先做完境内、再做境外。按理说利率市场化应该走在前面,但现在是人民币如火如荼、很多事情都在发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要加快利率市场化。
日报: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如何管理资本流入和流出是个大问题。
刘忆如:对,我们称台湾那时的经验为“甜蜜的负担”,因为资金一直在进来,可我们的市场尚未调整好,开放的速度也尚未调整好,有些“门”开着,有些“门”又想要关,可是外界不会等。所以造成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境外的资金一直在换成新台币,到台湾来买股票、买房地产。到后来资金撤出的时候,受伤很深。
日报:当时在台湾哪些“门”开着、哪些“门”关着?如果那时有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否可以避免那么多的热钱流入?
刘忆如:其实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从1986年开始,我们的贸易顺差占GDP高达30%。台湾经济规模小,这是原因之一。当时的时代背景是1985年时的《广场协议》,那时美元相对全世界货币都在贬值,新台币当然要升值,但出口商认为不能那么快升值,否则企业活不下去。这种情况下,新台币是超贬的。超贬就能带来更多贸易。贸易的有利并不是真正有益的,但由于报价能赚很多钱,所以就累积了很多贸易顺差,赚进非常多的美元外汇。
日报:那时台湾的汇率制度还没有市场化,但有波动区间,这和现在大陆的情况很类似。
刘忆如:对。所以我们那时凡是有资金流入,“央行”就购买作为外汇储备,但同时就会有新台币流出。所以货币供给增加得非常快,这些钱就去买股票和不动产。除此之外,当时美国给台湾很大压力让新台币升值,台湾“央行”就宣布称“新台币会缓慢升值”,这是个错误。因为这样就等于邀请全世界的资金都来换成新台币,导致了非常大的套利套汇空间,资金源源不断进来。
当时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民众无法参与套汇,而贸易商就通过凭证去银行借美元,出现了大量从境外银行借美元、到台湾抛售换成新台币,再去买股票或房产的情况。源源不断地借美元这个恶性循环,一直到1987年5月31日才停止,台湾“央行”当时宣布冻结银行外债余额,只能还不能借。10月1日“央行”尝试开放以观察市场状况,结果开放第一天就流入30亿美元,于是10月2日不得不再次关闭,因为显然市场还处于疯狂借美元的状态。那时新台币对美元已经升值到26了,等到市场心理稳定下来之后才逐步放开。之后仍有“一朝被蛇咬”的心态,所以后来很长时间内对于银行境外负债余额都不敢放开。我觉得这点倒有些太过保守了。
之所以当时央行采用缓慢升值的政策,是因为看见新台币有应当升值的趋势,但顾虑出口商,这样就放弃了很好的升值机会。40是不对,但拖那么久才升值到26,这个过程中很多贸易商能赚到很多钱。现在再看当时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可以给某些出口商一些补贴,帮助其转型,但不能因为少数利益而影响到整体政策。在制定汇率和利率这样大的政策时,一定要考虑的是怎样对整体经济最好。
银行准入不要太快放开
日报: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台湾有怎样的经验教训?
刘忆如:我们经历了两次利率市场化。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但那一次不是很成功,于是我们推行了第二波利率市场化。
第一波是存贷款一起放开,步骤是先用票券市场,即一年以内的短期票券,因为只有票券,所以只是少数人能看见的部门。这起了很好的“央行”指导作用。每一次波动区间的扩大都是由票券多少引导的。刚开始的三家“公营”票券公司在台湾利率市场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三家票券虽然是“公营”的,但其利率是自由的,一年之间调整了十几次利率幅度。我们的存款放款都有区间,“央行”规定了可以上浮下浮的区间,就可以在区间之内调整。区间本来很窄,不到10%,所以银行之间没有什么竞争性。后来逐步开放,区间就越来越宽。
日报:台湾放开利率管制后,利率一直在往下走,可能是由于资金过于充裕导致,但其他地区的经验显示,利率市场化的结果未必是利率走低。
刘忆如:对,要看时机。因为当时资金充沛,所以很快开放利率市场化,水到渠成。第一次是1985年前,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时机不是很好。
日报:但大陆未来一段似乎很难找到利率能一直往下走的时机,因为目前全球的利率趋势是往上走。
刘忆如:现在的趋势是往上走,所以很困难。我认为大陆别无选择的原因就是现在离岸市场已经有了发展,香港2013年的人民币存款已经破7000亿元,10月份台湾已经破1000亿元,伦敦达1400亿元。所以加起来就接近一个很关键的数字:1万亿元。在货币国际化时,1万亿元常常是个很重要的门槛,因为1万亿元意味着已经达到规模经济的程度,开始出现对于这个货币衍生性商品的需求。因为衍生品是场外市场,不需要得到任何批准就可以开始做。所以人民币在离岸如火如荼,就会有自己的定价。利率在境内外不同的时候,就会产生套利空间。所以人民币的利率可能会往上走一些,毕竟现在全球还处于低利率,未来只会往上,不会往下,所以还是要把握好时机。
日报:在台湾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放开银行准入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比利率市场化晚,在银行准入方面台湾有什么经验可以与大陆分享?后来的银行危机是否和银行准入门槛降低、过度竞争有关?
刘忆如:我觉得不要太快放开,要有一定顺序。台湾民营银行太多,申请的基本通过。相对于国际标准,台湾的申请门槛算是挺高的。可是富人很多,大陆今天更是这样。那时一次通过得太多,又恰好碰到很多台商都离开台湾,但台湾的银行不能跟着台商,都聚集在台湾,竞争激烈。银行一定要跟着客户走,大陆就没有这个问题。
日报: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存款保险制度是不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大陆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参考哪些模式?比如,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模式?
刘忆如:存款保险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无论钱是存在“公营”银行,还是存在民营银行,只要加入存款保险,钱都是保险的。我们当时的存款保险制度做得很好,的确很重要。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推出的,推出后大家逐渐了解,我觉得这也是民营银行推出的前提。台湾参照的就是FDIC的模式,我觉得大陆也可以这么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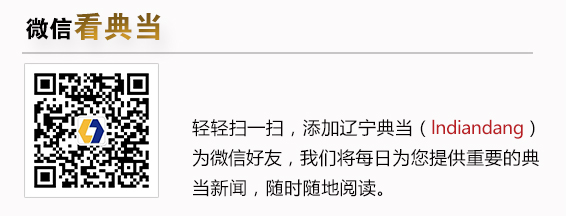
台湾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为中国大陆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谈到汇率和利率改革,刘忆如强调,不能因为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影响到整体经济政策。而低利率环境对利率改革比较有利。
她认为,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1万亿元是个很重要的门槛,意味着已经达到规模经济的程度,开始出现这个货币的衍生性商品,出现市场化的离岸利率,从而构成套利空间,迫使货币加快市场化进程。而大陆目前刚刚过了这个门槛。
关于银行准入,刘忆如认为,不宜太快放开,要有一定顺序。而一个好的存款保险制度安排很重要,更是民营银行准入的前提。
汇率改革需考虑整体利益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大陆正在推进包括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一系列金融改革。中国台湾在各项改革上都有不少相关的经验和教训。你认为台湾的经验对于大陆未来几年的改革有何借鉴意义?
刘忆如:我认为在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开放过程中,金融通常都放在最后一块,因为金融特别敏感,牵一发动全身。所以中国金融市场化开放,最需要注意的是顺序和速度。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像拉丁美洲在上世纪80年代金融开放时速度没有放对、顺序有点混乱。目前看来,大陆的基本方向是对的,顺序上也很注意。可因为外界的期待很高,不能等大陆慢慢地一步步来。例如利率市场化通常是优先于资本市场化改革,或者说是先做完境内、再做境外。按理说利率市场化应该走在前面,但现在是人民币如火如荼、很多事情都在发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要加快利率市场化。
日报: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如何管理资本流入和流出是个大问题。
刘忆如:对,我们称台湾那时的经验为“甜蜜的负担”,因为资金一直在进来,可我们的市场尚未调整好,开放的速度也尚未调整好,有些“门”开着,有些“门”又想要关,可是外界不会等。所以造成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境外的资金一直在换成新台币,到台湾来买股票、买房地产。到后来资金撤出的时候,受伤很深。
日报:当时在台湾哪些“门”开着、哪些“门”关着?如果那时有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否可以避免那么多的热钱流入?
刘忆如:其实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从1986年开始,我们的贸易顺差占GDP高达30%。台湾经济规模小,这是原因之一。当时的时代背景是1985年时的《广场协议》,那时美元相对全世界货币都在贬值,新台币当然要升值,但出口商认为不能那么快升值,否则企业活不下去。这种情况下,新台币是超贬的。超贬就能带来更多贸易。贸易的有利并不是真正有益的,但由于报价能赚很多钱,所以就累积了很多贸易顺差,赚进非常多的美元外汇。
日报:那时台湾的汇率制度还没有市场化,但有波动区间,这和现在大陆的情况很类似。
刘忆如:对。所以我们那时凡是有资金流入,“央行”就购买作为外汇储备,但同时就会有新台币流出。所以货币供给增加得非常快,这些钱就去买股票和不动产。除此之外,当时美国给台湾很大压力让新台币升值,台湾“央行”就宣布称“新台币会缓慢升值”,这是个错误。因为这样就等于邀请全世界的资金都来换成新台币,导致了非常大的套利套汇空间,资金源源不断进来。
当时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民众无法参与套汇,而贸易商就通过凭证去银行借美元,出现了大量从境外银行借美元、到台湾抛售换成新台币,再去买股票或房产的情况。源源不断地借美元这个恶性循环,一直到1987年5月31日才停止,台湾“央行”当时宣布冻结银行外债余额,只能还不能借。10月1日“央行”尝试开放以观察市场状况,结果开放第一天就流入30亿美元,于是10月2日不得不再次关闭,因为显然市场还处于疯狂借美元的状态。那时新台币对美元已经升值到26了,等到市场心理稳定下来之后才逐步放开。之后仍有“一朝被蛇咬”的心态,所以后来很长时间内对于银行境外负债余额都不敢放开。我觉得这点倒有些太过保守了。
之所以当时央行采用缓慢升值的政策,是因为看见新台币有应当升值的趋势,但顾虑出口商,这样就放弃了很好的升值机会。40是不对,但拖那么久才升值到26,这个过程中很多贸易商能赚到很多钱。现在再看当时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可以给某些出口商一些补贴,帮助其转型,但不能因为少数利益而影响到整体政策。在制定汇率和利率这样大的政策时,一定要考虑的是怎样对整体经济最好。
银行准入不要太快放开
日报: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台湾有怎样的经验教训?
刘忆如:我们经历了两次利率市场化。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但那一次不是很成功,于是我们推行了第二波利率市场化。
第一波是存贷款一起放开,步骤是先用票券市场,即一年以内的短期票券,因为只有票券,所以只是少数人能看见的部门。这起了很好的“央行”指导作用。每一次波动区间的扩大都是由票券多少引导的。刚开始的三家“公营”票券公司在台湾利率市场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三家票券虽然是“公营”的,但其利率是自由的,一年之间调整了十几次利率幅度。我们的存款放款都有区间,“央行”规定了可以上浮下浮的区间,就可以在区间之内调整。区间本来很窄,不到10%,所以银行之间没有什么竞争性。后来逐步开放,区间就越来越宽。
日报:台湾放开利率管制后,利率一直在往下走,可能是由于资金过于充裕导致,但其他地区的经验显示,利率市场化的结果未必是利率走低。
刘忆如:对,要看时机。因为当时资金充沛,所以很快开放利率市场化,水到渠成。第一次是1985年前,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时机不是很好。
日报:但大陆未来一段似乎很难找到利率能一直往下走的时机,因为目前全球的利率趋势是往上走。
刘忆如:现在的趋势是往上走,所以很困难。我认为大陆别无选择的原因就是现在离岸市场已经有了发展,香港2013年的人民币存款已经破7000亿元,10月份台湾已经破1000亿元,伦敦达1400亿元。所以加起来就接近一个很关键的数字:1万亿元。在货币国际化时,1万亿元常常是个很重要的门槛,因为1万亿元意味着已经达到规模经济的程度,开始出现对于这个货币衍生性商品的需求。因为衍生品是场外市场,不需要得到任何批准就可以开始做。所以人民币在离岸如火如荼,就会有自己的定价。利率在境内外不同的时候,就会产生套利空间。所以人民币的利率可能会往上走一些,毕竟现在全球还处于低利率,未来只会往上,不会往下,所以还是要把握好时机。
日报:在台湾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放开银行准入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比利率市场化晚,在银行准入方面台湾有什么经验可以与大陆分享?后来的银行危机是否和银行准入门槛降低、过度竞争有关?
刘忆如:我觉得不要太快放开,要有一定顺序。台湾民营银行太多,申请的基本通过。相对于国际标准,台湾的申请门槛算是挺高的。可是富人很多,大陆今天更是这样。那时一次通过得太多,又恰好碰到很多台商都离开台湾,但台湾的银行不能跟着台商,都聚集在台湾,竞争激烈。银行一定要跟着客户走,大陆就没有这个问题。
日报: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存款保险制度是不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大陆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参考哪些模式?比如,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模式?
刘忆如:存款保险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无论钱是存在“公营”银行,还是存在民营银行,只要加入存款保险,钱都是保险的。我们当时的存款保险制度做得很好,的确很重要。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推出的,推出后大家逐渐了解,我觉得这也是民营银行推出的前提。台湾参照的就是FDIC的模式,我觉得大陆也可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