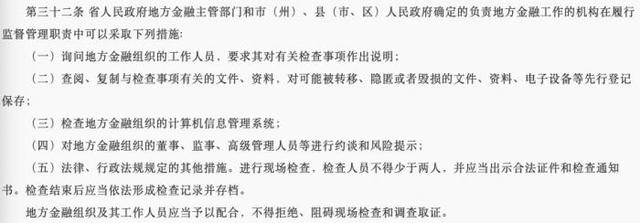公司向其股东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认定(3)
我们可能对解释出来的“例外”抱有怀疑:难道不可以直接把具体强制规范的违反后果同狭义无效联系起来,从而直接得出结论吗?首先,这种疑问实际上还是以强制规范违反禁止规则存在一个例外为逻辑前提的,只不过这种前提性的例外规则没有明确表示出来而已。否则,在具体强制规范没有明确效力后果规定时,就无法找到效力适用规范。其次,直接适用这种隐含而未明确的逻辑“例外”,会使得法律依据显得过远,不符合法律的安定性要求。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依赖完全不可见的解释关系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规范上的简略方法,不具有操作上的明确性。此外,强制规范的违反后果,在狭义无效之外,还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其他效力后果,比如无效以外的其他效力瑕疵直至完全有效等。如此丰富的效力后果,留给解释本身去解决,也同样欠缺规范适用上的明确性。因此,即便从否定的角度去思考,具体强制规范在适用上也必须以强制规范禁止规则为效力规范基础。
目的限缩解释,也是在奥地利法和瑞士法都没有规定规范目的保留条款情形下,两国理论所采取的共同解决方案。[33]德国有学者甚至认为,德国法上的规范目的保留条款规定的多余了,因为对原则规定的解释本身就足以解决问题。[34]
依据这一解读结论,§52(5)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并且具备了新的功能——具体强制规范适用的规范基础。因此,当我们说,某一合同尽管违反强制规范但却仍然应当有效的时候,我们不是以立法者的身份在创造法律,更不是无视法律,而是以法律适用者的身份在运用法律。因为,我们此时的结论是建立在合同法§52(5)基础上的法律适用的结果。正是在将具体强制规范与§52(5)结合适用时,我们才可以说,“根据合同法§52(5)的规定,该合同应该是有效的(或者无效的等)。”
可见,对法律作规范目的解释,帮助我们建立了我国合同法中的强制规范违反禁止的干预保留条款(或称,规范目的保留条款、但书条款、“原则-例外”关系条款)。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具体强制规范的规范目的决定了所需要的私法上的后果,§52(5)提供了适用这种私法后果的法律基础。
5、§52(5)的规范构成
如果我们把上述初步结论看作是目的解释的第一次作用的话,那么,我们沿着现在的结论继续往前走,就会发现目的解释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毫无疑问,合同法§52所规定的无效,是一种狭义上的无效,属于绝对强制规范。这是由于对该条规定作了限缩性的目的解释的缘故。因为根据一般的法理要求,对法律和公序良俗违反的行为,是最严重的与法律制度相冲突的行为。这种严重行为只有与最严格的私法上的否定后果相匹配,才相适合。强制规范违反禁止和公序良俗违法的禁止也就属于法律制度中最为严厉的法律武器。[35]此时的无效,原则上属于完全无效,自始无效,不可补救,不可转换,也不可通过确认来恢复效力,是一种典型的无效。[36]这种效果的认识,只有通过对§52作目的限缩的解释才能实现。这从罗马法关于无效制度的萌芽发展过程也可以得到启发。因为在罗马法中并没有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民法上的无效制度,因此甚至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专门术语。但是,被称之为nullun,或者nulliusmomenti,或者inutile的民事上的无效行为,必须根据行为的本质和目的来对其效力加以否定。[37]在法律制度发展之初,一种具体制度效果的获得就是通过对行为的本质与目的的解释来实现的。现代法律制度建立之后,在具体的制度规范不能直接显示其法律关系时,我们还是得像原始的法律适用一样,采用同样的方法。对此,我们也许可以小心地说,这种返朴归真的做法正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根本途径,一种无法逃避的最终唯一正确的认识方法。总之,正是对§52作第二次的目的解释,使我们得出了对§52的进一步限制。
强制规范可以分成绝对强制和相对强制规范,无效也有不同程度之分。绝对强制规范导致完全无效,相对强制规范导致不完全的其他效力瑕疵和效力没有瑕疵的完全有效。那么,我们又是如何区分这些不同的效力情形的呢?答案是:还是根据规范目的解释。我们还是必须通过规范目的来将强制规范违反的不同程度的后果区分开来。区分的法律形式意义在于,§52所肯定的无效情形是在最狭义上使用的,是指对于绝对强制规范适用的无效,一种狭义上的无效。其他违反强制规范的情形,从效力待定等各种效力瑕疵直至完全有效,都是§52没有明示的干预保留规范所要调整的范围,属于“法律并不以之为无效”的情形。
从纯粹字面本身来看待§52(5)的话,将这里的无效解释成包括效力待定等所有效力瑕疵情形在内的话,在技术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第一,它不甚符合强制规范的绝对强制性特征;第二,特别是它会同§52其他各项的法律后果不协调。因为合同法在§52中对于所有5项只共同使用了一个“无效”用词,因此,该“无效”在含义上就应该有对其他各项的共同的适用性。比如§52(4),就要求是绝对的自始的无效,即狭义上的无效。这可以说是一个局部的系统解释。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才有必要把§52(5)中的“无效”限制在一个绝对狭义的强制规范及其后果上。当然,就具体的效力情形加以区分总是必要的,这里解释的只是把完全无效以外的其他效力瑕疵归入§52(5)的“原则”部分还是“例外”部分而已。所以,对于区分不同效力后果的功臣——“规范目的解释”,却总是少不了的。
可见,规范目的解释,又使强制规范违法禁止的各种后果得以区分开来。这是该解释方法在强制规范适用中的第三次作用。
至此,通过规范目的的解释方法,我们从§52(5)中区分出了规范目的保留条款,建立了关于强制规范违反禁止的完整的规范基础。针对这一规范基础,通过规范目的解释,我们进一步明确了该规范基础的规范构成,即,从§52(5)中得出了“无效”的绝对强制性质;从§52(5)的规范目的保留条款中看到了除完全无效后果以外的其他所有不同的效力后果。总之,通过规范目的解释,我们在§52(5)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我国现行法上关于强制规范违反禁止规则的完整体系,确立了一个适用强制规范违反禁止的完整的法律基础。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目的解释在本文的问题研究中,就像魔杖一样,可以在你任何需要它的关键时候突然现身,大展身手。就像联邦德国的司法判例和学说资料都一致认为的那样,只能通过禁止规范的规范目的(SinnundZweck)才能确定无效。[38]因为,§134并不是径自规定违反法律禁令的行为无效,而只是规定,行为在“法律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才是无效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从§134规定本身推导出无效的后果,而只有通过对有关法律禁令的解释,才能得出这种无效性的结论。[39]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反复凸现目的解释,用意不在于作魔术表演,或文字游戏,而是在分析§52(5)的功能结构的同时,也特别彰显法律适用时“法依据”的必要性。就是说,法律的适用离不开法律规范本身。我们可以合理解释它,构建它,但却不可以忽略它,更不可以践踏它。这应该至少首先成为法律人的法律情感(Rechtsgefuehl[40])。当它成了全社会人们的法律情感时,社会就有了一个牢固的法律意识,我们可能就会自觉地去尊重法律,尊重法律实践,也就可能不会再存在一个像当今这样几乎都形成为社会问题的缠讼现象。
可见,以合同法§52(5)为基础的规范基础是在具体强制规范不同后果需求的促动下,通过对该项作多层次的目的解释确立的。其规范构成(AufbauderRechtsnorm)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但是(强制性)法律并不要求无效的除外”,即,一个“原则+例外”的体系。该规范结构的内容(inhaltlicheNormstruktur)是,“原则”中的无效,与合同法所使用的所有“无效”用词含义一致,是指狭义上的无效,一种确定的、对所有人的、溯及的和原则上不可补救的无效;而“例外”情形下的效力效果则包括狭义无效以外的所有其他效力瑕疵情形,直至完全的有效。这可以用公式形象地表示为:
规范基础=规范构成+内容结构
完整的强制规范违反禁止规则的规范体系(Normensystem)是,由以合同法§52(5)为基础的规范基础(Normgrundlage)和具体(被违反的)强制规范(konkretezwingendeNorm)构成的二元结构。用公式表示就是:
规范体系=规范基础+具体强制规范
这是要求,在具体适用时,首先要对行为所违反的具体规范作出判断,在肯定其为强制规范之后,再将该具体强制规范函摄入合同法第§52(5),以进一步判断其对私法上行为后果的影响。
(三)具体的判断步骤与判断方法
基于上述分析,强制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关系,除法律对其后果有明确规定以外,在具体判断方法上,首先要对具体所违反的规范是否具有强制规范性质作出分析判断。[41]不属于强制规范的,当然不影响合同效力;属于强制规范的,仍应进一步判断该规范是否应该进一步影响到合同的效力,还是仅仅由其他法规,主要是公法规范,给予罚款等其他处罚即可以达到目的,或者强制的内容仅仅涉及合同履行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外围问题,或者强制的仅仅是一方当事人等等,来具体判断。[42]并且,对于已经履行的合同,还要特别考虑已经履行的事实对于禁止效果的消除以及基于履行所产生的当事人之间特殊信赖利益的保护等因素,对合同效力予以的特别考虑。
对于具体违反规范的分析判断,通常在字面含义不能明确指明时,同样需要用规范目的的解释方法。对于具体场合下的强制规范,则要通过利益衡量的方法,即对根据规范目的所解释出的具体强制规范所保护的利益与基于合同的各种利益(意思自治、合同效力维护等)作综合的利益比较,来进一步判断是否需要否定违反行为的私法效果。
具体而言,在根据具体强制规范的规范目的分析出其所保护的利益之后,应对具体规范目的所保护的(也是合同所破坏的)利益和合同自由等合同效力维护利益这两大基本利益阵营作出利益比较。这一操作方法最多可能存在三个判断层次,即宏观的(抽象的)一般利益比较层次,一般的实践性优先考量和具体的事实上的利益关系限制。在任何一个判断环节,如果能够得出合同效力维护利益应该得到优先保护的结论时,判断即告终结,无须再作其他环节的判断,否则须依次判断,如果存在第三个层次的判断可能的话。具体做法如下。首先,按照强制规范所调整的生活事实所可能受到的典型危险的程度(危险性标准)与合同效力维护利益作抽象的优先性比较(第一层次),然后再对经过比较后认为具有抽象优先性的规范保护利益进行实践的优先性考量,即用规范目的的预防性标准来进一步判断具有抽象优先性的强制规范是否从预防性角度看有予以比合同效力维护利益优先保护的必要性(第二层次)。实践性优先考量采用的方法可能会因具体情形的不同而有别,但内部矛盾性分析方法和结果实现的可能性方法,是基本判断方法。对经受住实践性优先考量检验后的强制规范,才可以初步认为,其具有比合同效力维护利益更为优先的保护价值,也就是说,合同效力才会受到强制规范的影响。不过,完整的判断到这里还并没有结束,有时检验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比如在已经履行了的合同中,由于履行事实可能改变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状态,改变了强制规范所要保护的利益关系,此时,可能需要对法律和平、法律的安定性以及当事人之间的诚实信用给以特别的关注和保护。这些都足以构成在特定场合下否定在实践性优先考量检验中得到肯定的强制规范保护利益的优先性(第三层次)。此外,在整个的利益衡量过程中,我国现阶段对于私法自治精神培养和国情因素扣除的观念也要始终贯穿于判断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规范目的解释方法对中国国情的适应,才能使强制规范这一带有强烈的国情色彩的法律政策与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私法制度相适应。[43]
总之,强制规范的效力关系判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解释、判断过程,是一个需要法官在司法中谨慎驾驭的司法领域。这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都是同样充满危险性和挑战性的法律适用领域。它需要法官对法律的全面和正确的理解;需要法官对法政策的高度把握;需要法官有良好的利益辨别能力和判断意识;需要法官有足够的智慧和胆识。严肃的挑战性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回避或者放弃适用上的任何努力。相反,它要求我们应当加倍认真地对待它,要